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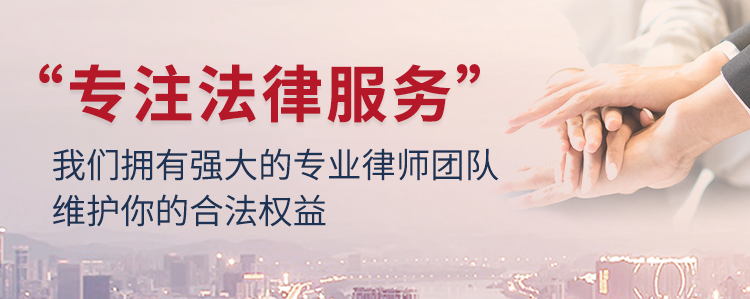
2025-07-25 15:00:59
文章来源: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
阅读:151
1986年的北京丰台,尘土在路尽头扬起时,李长河背着半袋红薯从砖窑厂往家赶。作为家里的长子,他比弟妹们早几年尝到生活的重量,十五岁起就跟着村里的泥瓦匠当学徒,掌心的茧子厚得能磨亮砖面。
二十二岁那年,李长河攥着攒了七年的积蓄,走进村委会办公室。那张《村民申请盖房占地审批表》上,他的名字落在“使用权人”一栏时,笔尖在纸上顿了顿。批下的74号院宅基地,成了他此后半生的锚点。几年后,四间北房在空地上挺立起来,一砖一瓦,皆是他汗水砸出的印记。红砖墙砌好了,油毡纸铺上了屋顶,他成了家,烟火气便在这小小的院落里扎了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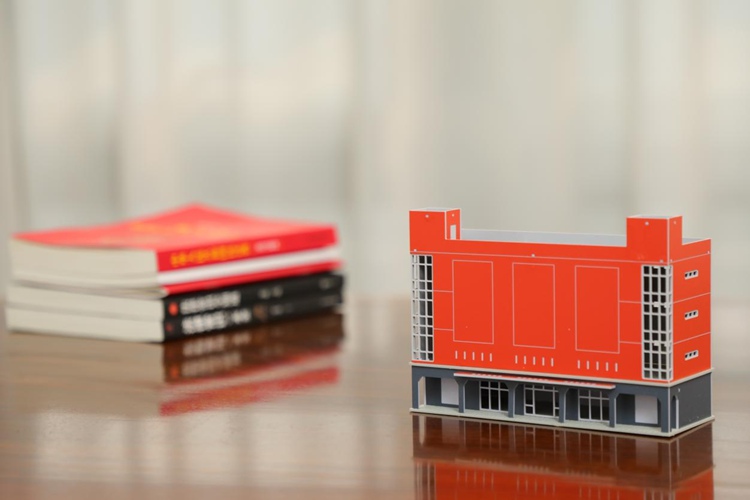
小弟李长明彼时尚且年少,无片瓦遮头。李长河默许了他搬进这个小院,住进西头那间小屋。屋檐下多了一人,他望着小弟年轻的身影在院里进出,心中宽慰,只道是骨肉至亲,同在一个屋檐下互相照应也是寻常。院里的老枣树绿了又黄,父母在邻近的72号院日渐老去。
2015年至2017年父母相继去世后,72号院空了下来,李长河才第一次郑重地对李长明提起:“长明,搬去72号院吧,那院子宽敞些。”话音落在安静的院落里,却如同石沉深潭,李长明默然以对,纹丝不动。
更令他心寒的是,不知从何时起,三个妹妹李红梅、李红兰、李红竹竟也认定这74号院属于父母遗产,人人都有份,还搬回了74号院居住。李长河拿出那张早已泛黄、折痕明显的宅基地审批书,指尖反复摩挲着上面自己的名字,试图唤起她们的记忆。然而,三姐妹只是瞥了一眼,便称村委会的章不算数,血缘才是最可靠的依据。前来调解的村委会干部来了又走,苦口婆心的劝说终究是徒劳无功。
李红梅、李红兰、李红竹,再加上住在院中沉默却执拗的李长明,这四人的身影在74号院投下的阴影,一天比一天更沉重地压在李长河的心头。无奈之下,李长河前往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寻求帮助。律所指派律师王栋、贺丽影代理此案。
接受委托后,冠领律师指导李长河收集关键证据调取《村民申请盖房占地审批表》,明确74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系李长河;整理建房时的材料采购凭证、工匠证言等,证明房屋由他全款出资建造;获取村委会及街道办事处的说明,佐证宅基地权属清晰。
律师分析,弟弟妹妹们可能会以“宅基地为家庭共有”“房屋系父母出资”为由抗辩。为此,冠领提前准备应对方案:针对宅基地归属,强调审批表明确记载使用权人为李长河,且村委会已多次确认;针对出资问题,结合李长河当年的工作收入、建房时间线,以及弟妹们未能提供任何出资证据的情况,形成完整证据链。基于证据,律师确定核心诉讼主张74号院北房四间归李长河所有。准备就绪后,律师代理李长河向法院提起诉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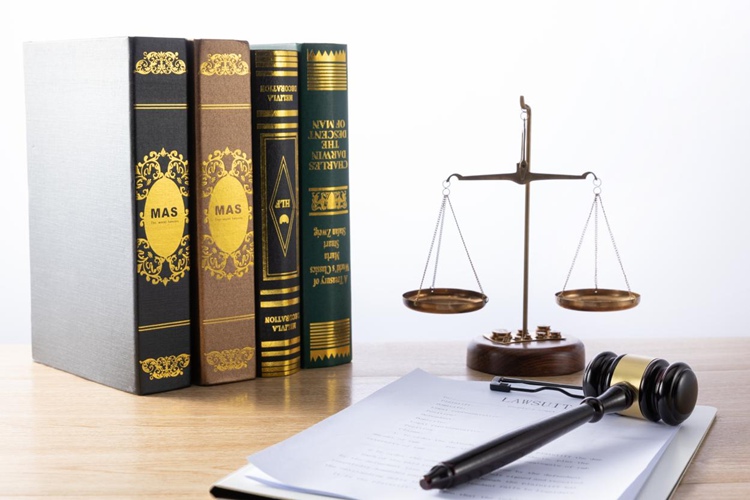
庭审中,李长明等四人提出抗辩:主张74号院是以家庭名义申请的宅基地,房屋由父母出资建造,应作为遗产分割。
冠领律师从容应对,出示《村民申请盖房占地审批表》原件,结合村委会证明,明确指出审批表上清晰记载使用权人是李长河,且无其他家庭成员名字,宅基地权属归属明确;详细陈述李长河的出资事实,提交当年的工资流水、建材购买收据,以及邻居和建房工匠的证言,证明1986年建房时李长河已具备经济能力,且房屋确由其全款建造;强调父母名下另有72号院房屋,李长明等四人对74号院主张权利无事实依据,更不符合“谁申请、谁出资、谁所有”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惯例。
律师还指出,村委会曾主持调解并明确74号院权属,李长明等四人拒不接受调解、长期霸占房屋的行为,既无法律依据,也违背家庭伦理。
2025年6月,经法院审理,判决74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系李长河。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,李长河感慨万千。这场纠纷不仅关乎房屋归属,更牵动着手足亲情。冠领律师以专业的法律分析和扎实的证据准备,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,也为化解家庭矛盾画上了公正的句号。(文中除冠领律师外均为化名)
撰稿人:毛梦遥
审核人:段光平